疼痛部(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 豆瓣2023年度作者,“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”) 电子书下载 PDF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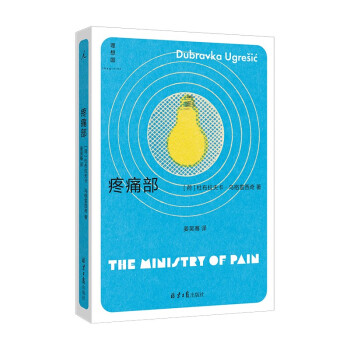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,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,我像童话里的龙一样吐出舌头,然后它就分叉了:克罗地亚语、塞尔维亚语、波斯尼亚语、斯洛文尼亚语、马其顿语……
一门如此令人痛苦的语言,一门从来没有学会描述现实,与人对于现实的内在体验同样复杂的语言,能够讲故事吗?
一开始都是这样。或者那样。他们做了那件事,去了那里,然后来到荷兰。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。短短的“战后”发生了太多的事,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。一切都坏掉了。地点和时间分成了“以前”和“后来”,生活分成了“这边”和 “那边”。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、父母、家人、朋友,乃至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。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,他们被抛回了自身。
在媒体化的世界里,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,以朱丽叶·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,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。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。
疼痛是无言的、无用的,却唯一真实的证人。
同类热门电子书下载更多
- 恶心
- 多谢不阅(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 豆瓣2023年度作者,“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”)
- 道德故事集 诺奖布克奖得主库切短篇小说集首次引进 围绕老年独居女性话题 外国文学慢人黑铁时代
- 静静的顿河(全三册,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。只要还有人做正派的人不正派的时代就会被改变)
- 刀锋
- 守望者·文学:王国
- 双语译林: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(附英文原版书1本)
- 东野圭吾 时生 2023新译本 父母能否自信地问孩子:作为我们的孩子 你觉得幸福吗?易烊千玺推荐
- 大师和玛格丽特(2024)
-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(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 豆瓣2023年度作者,“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”)
- 强风吹拂(2023版)
- 希望庄 日本推理女王宫部美雪强势新作 横扫3大推理榜单
- 译文经典:愤怒的葡萄 包揽美国国家图书奖、普利策小说奖 [The Grapes of Wrath]
- 疼痛部(杜布拉夫卡·乌格雷西奇 豆瓣2023年度作者,“你从未听说过的十个伟大的作家之一”)
- 绿房子(诺奖得主略萨震撼世界文坛的代表作,一所妓院的兴亡盛衰折射一个国家的深层历史)(精装)
- 月亮与六便士(毛姆代表作)
- 杀死一只知更鸟(2023)
- 鼠疫+西西弗神话+局外人: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代表作品集(套装全三册)
- 西西弗神话(诺奖得主加缪代表作) [Le Mythe de Sisyphe]
- 动物农场
Copyright © 2025 by topbester.com.
All Rights Reserved.
沪ICP备14027842号-1
All Rights Reserved.
沪ICP备14027842号-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