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 电子书下载 PDF下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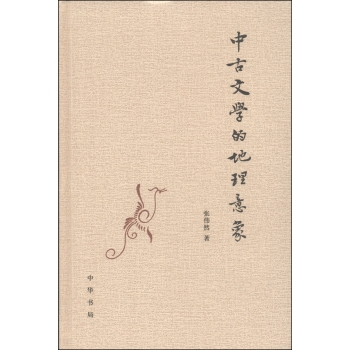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不过相对而言,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特别关注一些类型化的地理意象。这些意象之所以能类型化,显然是可以反映一些特定的文化观念,具有特别丰富的文化地理价值。
现在略陈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的学术构想。
第一章“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”,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。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,已见于上述。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,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。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,属于断代性质;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,覆盖了全国。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,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,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。
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,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。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,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,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。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。况且,就资料而言,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。例如《史》、《汉》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、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,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。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,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,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。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,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。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。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,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。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,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;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。
限于时间和精力,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。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,衣冠文物之盛,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。同时,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,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。因此,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,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第二章“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”,内容分四部分,围绕的是“江汉”和“洞庭”两个地名,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。
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,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,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,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,而不关心一般情形,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。例如,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“特指”与“泛指”,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。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“江汉”指巴蜀,便以为“江汉”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。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,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。
更要命的是,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,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。例如,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“西汉水”,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、有汉,因之可称“江汉”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,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“吴”。而全然不顾“江汉”、“吴”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。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,而是在创造历史了。要研究历史,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,得做归纳。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,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,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。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、合理、可信的。
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,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,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,不可一日或缺的。因此,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,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。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,一目了然,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。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、时代往往虚构,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,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,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。
第三章“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”,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。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,特别在文学史界,出现了若干种专著。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,因而其中的“地理”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,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。事实上,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。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,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,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。
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,第一节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,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,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。其中第一节视角比较独特,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,相关研究都很少;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,特别是关于“潇湘”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、潇湘八景,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。其中,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,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,毕竟非其研究主旨;而关于“潇湘”语汇的探讨,则必然要对“潇湘”意象进行分析。
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。从文学角度探讨“潇湘”意象,虽然也不能不考量“潇湘”作为地理实体,但目标还是其中的“意”,如恨别思归、愁苦闲适之类①。而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,关键是考察其中的“象”;即,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、场景感。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、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“公共领域”的“空间”,而是有长宽高、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。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。
在中古文学中,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,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。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。例如中古乐府中的“巫山高”、“陇头水”,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“淮南落木”,以及唐宋词牌中的“望江南”、“八声甘州”等等,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。
第四章“‘禽言’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”,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。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,然后对其展开讨论;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,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。
毋庸赘言,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、颠覆、转化的过程。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,更受制于文化取向、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。环境产生刺激,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。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。
中古以前,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。《诗》三百虽然以“关关雎鸠”开篇,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。而且,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。诗中有“鸟言”,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,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。因而,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,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,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、山水诗。中唐以后,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,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。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。酝酿到北宋,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。
现在略陈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的学术构想。
第一章“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区域”,属于感觉文化区的研究。之前笔者做过一项湖北的工作,已见于上述。湖北那项研究在空间上是一个区域,时代则从先秦一直通下来。这一章在时间上只包括唐,属于断代性质;空间上就没有再截取,覆盖了全国。这是参考谭其骧先生生前的理路,做两个相互对称的样本,以期对于感觉文化区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建立纵横两方面的参照。
以往学界对于文化区的探讨,主要是基于形式文化区。那种研究看起来很客观,因为每个区都是根据某项具体指标而划出来的,不是主观认同出来的。但选取指标本身是一项不免主观的工作。况且,就资料而言,现存史料的分辨率显然不可能一致。例如《史》、《汉》中记中原地区的风俗连宋、卫都可以分得很清楚,而广大的南方楚越之地则大而化之。因此笔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,对于历史文化区域的研究,感觉文化区比形式文化区更有意义。因为前者是通过古人的认同而复原出来的,它本身就是当时文化的一部分。而且是结构性的一部分。曾经用于指导古人的日常生活,并深刻影响其对世界的认知。形式文化区当然也有意义,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求证的意义;它对今人的意义可能更大于对古人的意义。
限于时间和精力,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对感觉文化区只讨论了唐代。但有唐绵延近三百年,衣冠文物之盛,影响所及并不止于它实际存在的那段时间。同时,感觉文化区大多由来有自,形成之后也并非朝夕可改。因此,希望本章不仅对中古时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,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时期的相关探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第二章“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”,内容分四部分,围绕的是“江汉”和“洞庭”两个地名,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空间逻辑的问题。
文学史研究对于历史地名向来重视,但由于其目标只在读通文学作品,带有很强的实用倾向,因而文学史学者所做的地名考释往往只强调具体语境,而不关心一般情形,不关注历史地名本身的规则。例如,他们不太注意区分地名的“特指”与“泛指”,也就是地名的本义与引申义。以至于见到杜甫在某首诗中用“江汉”指巴蜀,便以为“江汉”这一地名中本来就有指巴蜀这么一个义项。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地名,活生生被他们硬劈成两个。
更要命的是,他们还会从个人的想象出发,对历史地名作出一些纯逻辑的推论。例如,他们注意到嘉陵江有条支流在某些文献中曾被称作“西汉水”,便说嘉陵江流域有江、有汉,因之可称“江汉”。他们注意到三国时孙吴曾领有今湖南省境,便断定今湖南在历史上亦可称“吴”。而全然不顾“江汉”、“吴”这两个地名在历史上的实际使用情况。这从实质上已不是在研究历史,而是在创造历史了。要研究历史,这样做演绎是不行的,得做归纳。得从古人对某地名的具体用例中,找出其得名的确切依据,以及其使用的实际情形。那样的结论才是科学、合理、可信的。
近年笔者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,地理在古代是一门很实用的学问,是古人日常生活所需,不可一日或缺的。因此,从地名之间的空间关系,可以对文学作品作出一些基本判断。由于空间关系很直观,一目了然,通过空间逻辑得出的判断往往比其他逻辑更过硬。中古时期的小说对人物、时代往往虚构,而对空间场景却大多采取征实的态度,以至于史家经常引小说作为空间史料,这应该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点。
第三章“类型化文学意象的地理渊源”,是笔者关于文学地理的一种尝试。近年来文学地理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,特别在文学史界,出现了若干种专著。但那些研究一般都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统计分析,因而其中的“地理”往往只体现为一种分布态势,或者是作为背景的人文社会环境。事实上,地理因素完全可以参与文学创作。它可以成为作家的灵感,作家发挥想象力的凭据,从而形成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类型化意象。
本章分三节讨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地理意象,第一节巫山神女为虚拟文学人物,第二节潇湘为一文化地域,第三节竹林寺传说为具有特定文学内涵的空间类型。其中第一节视角比较独特,第三节内容较为稀见,相关研究都很少;而第二节则学界颇多相关成果,特别是关于“潇湘”语汇以及绘画中的潇湘图、潇湘八景,近年发表的各种论著简直令人目不暇接。其中,关于潇湘图画的研究比较偏向艺术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,虽然也会涉及潇湘意象,毕竟非其研究主旨;而关于“潇湘”语汇的探讨,则必然要对“潇湘”意象进行分析。
在这里可以看出视野的分殊。从文学角度探讨“潇湘”意象,虽然也不能不考量“潇湘”作为地理实体,但目标还是其中的“意”,如恨别思归、愁苦闲适之类①。而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作为一项历史地理学研究,关键是考察其中的“象”;即,潇湘作为一个地理空间而给人留下的空间感、场景感。这种空间感不是哲学、社会学意义上用以形容“公共领域”的“空间”,而是有长宽高、有声光色的物理空间给人的感觉。《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》尤想揭示其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。
在中古文学中,类型化的地理意象非常多,以往很少加以专门探讨。这方面还需将来继续努力。例如中古乐府中的“巫山高”、“陇头水”,唐人吟咏中经常出现的“淮南落木”,以及唐宋词牌中的“望江南”、“八声甘州”等等,都值得展开作专题探讨。
第四章“‘禽言’与环境感知中的生态呈现”,旨在讨论地理意象的深化过程。前三章基本上是将地理意象看作静态概念,然后对其展开讨论;而这一章则以鸟声为中心,着重探讨地理意象的动态变化。
毋庸赘言,地理感知是一个不断对既有知识进行更新、颠覆、转化的过程。其中既受制于环境本身,更受制于文化取向、知识背景等人文因素。环境产生刺激,文化背景决定接受及转化能力。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反馈过程。
中古以前,中国文学对于鸟声的感知非常单薄。《诗》三百虽然以“关关雎鸠”开篇,但其中的鸟声单调无比。而且,字里行间的人鸟关系非常淡漠。诗中有“鸟言”,但纯粹只是诗人的想象,与环境感知中的鸟声无关。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唐前期。因而,永嘉丧乱后大量北方诗人移居南方,新鲜的地理环境刺激他们只是在视觉上有所发现,由此在中国文学中兴起田园诗、山水诗。中唐以后,迁流到南方的北方诗人开始用听觉感知环境,这才发现鸟声对于环境的价值。于是人鸟之间的感情距离也大为拉近。酝酿到北宋,终于由自小与禽鸟相亲近的南方诗人写出成熟的禽言诗。
同类热门电子书下载更多
- 礼记译解 精装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局自营正版简体横排标点版
- 问题与方法: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(增订版)(三联讲坛)
- 诗经心读
- 历代杭州西湖诗词一百首(中英对照)
- 红楼梦的真故事(周汝昌给大家讲红楼梦未完故事)
- 中国历代诗歌选 套装共四册
- 周易兼义(套装上下册)
- 额尔古纳河右岸+白鹿原
- 许译中国经典诗文集-道德经(汉英)(新) [Laws Divine and Human]
- 八十年代访谈录
- 仪征刘申叔遗书(精装全15册)
- 常识课
- 重返:三国现场(签章钤印版)
-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集:北京折叠
- 坚如磐石
- 冰心散文 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(一书读懂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散文的精粹,辅以导读及十余幅插图)人民文学出版社
- 冰心儿童文学作品集(全3册 小学生课外读物 11-14岁图书 四五六年级儿童文学书籍)
- 谁是我,谁是你?伽达默尔谈策兰《呼吸结晶》
- 越境——“鲁迅”之诞生
- 文献新视域
Copyright © 2025 by topbester.com.
All Rights Reserved.
沪ICP备14027842号-1
All Rights Reserved.
沪ICP备14027842号-1